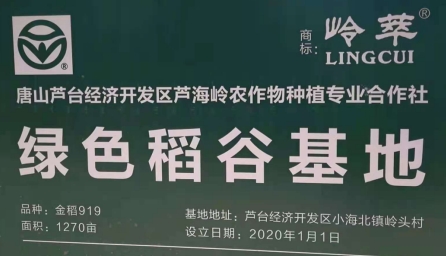“生死戀”是陽(yáng)江近年時(shí)興的一道菜肴,其實(shí)就是咸魚(yú)蒸鮮魚(yú)。據(jù)說(shuō)有一次漁民在出海做飯時(shí)剛做到鮮魚(yú)時(shí)發(fā)現(xiàn)沒(méi)有鹽了围婴,便想出了一個(gè)急招:把咸魚(yú)放進(jìn)去與鮮魚(yú)一起蒸德频,結(jié)果發(fā)現(xiàn)味道很特別宦衡,這個(gè)菜就傳了下來(lái)躏救。咸魚(yú)與鮮魚(yú)蒸出來(lái)的魚(yú)汁披腻,浸著細(xì)細(xì)的姜絲民沈,用以撈飯,令人回味無(wú)窮稼炉。
“生死戀”一條海魚(yú)的死生契闊犹喜。
海邊生活的人們每天都要面對(duì)魚(yú)的問(wèn)題,怎么去捕魚(yú)草嫉,怎么去吃魚(yú)阎敬,還包括怎么處理在保存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那些消費(fèi)不了的魚(yú)险锻,所以咸魚(yú)可以看做一種悠久的海洋文化,一個(gè)地方捕魚(yú)吃魚(yú)的歷史足夠悠久了魄帽,那么吃咸魚(yú)的伴生文化也就會(huì)發(fā)達(dá)起來(lái)现喳。
在內(nèi)地人把咸魚(yú)視作“短缺時(shí)代配給品”的時(shí)候,廣州人已經(jīng)知道咸魚(yú)的審美空間可以很廣闊了犬辰,“咸魚(yú)貴過(guò)雞”嗦篱,說(shuō)的就是在廣府食客心目中一條好咸魚(yú)的價(jià)值,然而這一切并沒(méi)有海邊的人們來(lái)得那樣自然和從容幌缝。
不必去遐想什么《人鬼情未了》和《胭脂扣》的風(fēng)月灸促,這道菜的做法其實(shí)很簡(jiǎn)單,就是把切好片的梅香咸魚(yú)和新鮮海魚(yú)逐片間隔起來(lái)蒸涵卵,魚(yú)的前世今生兩種迥然不同的鮮味交織混淆在一起浴栽,便成了筵席上的一道大菜,在陽(yáng)江當(dāng)?shù)馗邫n的長(zhǎng)江國(guó)際酒店里轿偎,“生死戀”的名頭堂而皇之地出現(xiàn)在菜單之上典鸡。
在饕客的評(píng)判標(biāo)準(zhǔn)中,咸魚(yú)彌補(bǔ)了鮮魚(yú)略顯單薄的味道坏晦,而鮮魚(yú)?=?又填補(bǔ)了咸魚(yú)缺少的口感萝玷,這是一種系統(tǒng)內(nèi)的補(bǔ)充和完善。而在更多的遐想中昆婿,這是一種類(lèi)似講故事的戲劇策劃立骄,人對(duì)食物的精神需求是多方面的,既有莊臣所說(shuō)的沿海居民對(duì)咸鮮味覺(jué)的執(zhí)著追求贞倒,也有一種人情世故中幻想的本能潘娄。
每一個(gè)地方都有其獨(dú)特的生態(tài)密碼,陽(yáng)江這地方還有一種號(hào)稱(chēng)獨(dú)此一處的“墨魚(yú)膏”汇割,這是一種用大墨魚(yú)的卵發(fā)酵而成的“超級(jí)咸魚(yú)”,它可以令“逐臭之夫”欣喜若狂勘职,也能讓幽蘭雅士退避三舍恋得,由于制作工藝的繁瑣和食材的取之不易,這種很唐突的美味即使在陽(yáng)江也不是隨處可見(jiàn)略菜,只有棲海的原住民還會(huì)不時(shí)小批量地制作一些來(lái)自己享用此妙。用墨魚(yú)膏來(lái)燜煮豬的五花肉,會(huì)令你忍不住四處尋找白米飯來(lái)“與子偕老”池粘。
死生契闊继韵,那是文學(xué)對(duì)生活的記錄。
一條發(fā)酵過(guò)的咸魚(yú)胆誊,是餐桌上對(duì)生活的回味一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