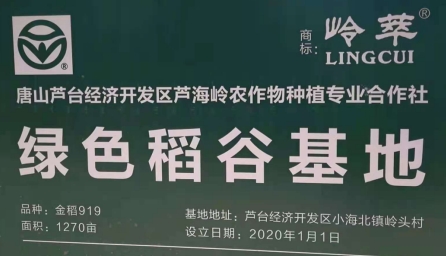今人賞櫻已成風(fēng)氣雁巾,那么一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是否賞櫻呢被处?是女阀,也不是。古代的中國人確實(shí)也賞“櫻”,并且歷史相當(dāng)久遠(yuǎn)。不過這里的“櫻”和今日廣為種植的櫻花不盡相同——它是櫻桃。

年年歲歲花相似宋睦,歲歲年年人不同。今人賞櫻已成風(fēng)氣腊拍,那么一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是否賞櫻呢琐侣?是,也不是呆淑。古代的中國人確實(shí)也賞“櫻”汇径,并且歷史相當(dāng)久遠(yuǎn)。南朝王僧達(dá)有詩云“初櫻動(dòng)時(shí)艷罗卿,擅藻灼輝芳史隆。緗葉未開蕊,紅葩已發(fā)光”曼验,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事了泌射。不過這詩里的“櫻”和今日廣為種植的櫻花不盡相同——它是櫻桃。
魏晉南北朝時(shí)鬓照,櫻桃作為庭院觀賞樹木并不罕見熔酷。《晉宮閣名》中說:“式乾殿前櫻桃二株豺裆,含章殿前櫻桃一株拒秘,華林園櫻桃二百七十株×舸ⅲ”華林園歷經(jīng)六朝翼抠,櫻桃尤其聞名。南朝宋的江夏王劉義恭得到了御賜華林櫻桃获讳,種在廳堂前阴颖,然而一入夏就惹了不少蟬,他不得不命人將蟬粘下來丐膝。
今天我們說到櫻桃孽衩,首先想到的是它果實(shí)紅艷可玩。古人不僅愛果實(shí)焕徽,還愛它早春時(shí)綻放的花朵陌沟。唐太宗《賦得櫻桃》開篇說“華林滿芳景,洛陽遍陽春”竹恃,就是從春天的櫻桃花講起截巢。《清異錄》載肘勾,宋朝的張翊曾經(jīng)戲作《花經(jīng)》呻蚪,品評群芳,分為九品九命箫废,當(dāng)時(shí)人普遍認(rèn)為他的品評很是恰切础姚。《花經(jīng)》中櫻桃被列為四品六命譬功,與菊花填恬、梅花等同品,這么看來奋隶,在當(dāng)時(shí)的共識(shí)中擂送,櫻桃花已有了相當(dāng)?shù)挠^賞價(jià)值了。
文人造園往往寄托雅趣唯欣,所以梅蘭竹菊這樣的“君子”在布景中屢見不鮮嘹吨,而櫻桃若是種得好,也能成為園中一景黍聂。明代王世貞造弇山園躺苦,園中有一寬廣庭院,王世貞本欲移栽五棵洞庭樹产还,布置出“五老峰”之景匹厘,未能實(shí)行,便改種櫻桃脐区,起名“含桃塢”愈诚。他說櫻桃的果實(shí)一年能解一次饞,而花也足以“飽目”(含桃成歲得一解饞牛隅,花亦足飽目)炕柔。“飽目”這個(gè)詞古已有之,不過此處和解饞并舉触法,有一種俳諧感漂烂。日本的賞花旅游廣告中喜用“満喫”這個(gè)詞,字面上也是吃飽喝足之意展稼。見花盛而覺飽腹束多,大概是一種人類共有的通感吧。
“紅粉風(fēng)流俩堡,無逾此君”
在娛樂手段還不夠高科技的古代拳股,賞花就是古人重要的娛樂活動(dòng)。從唐代詠櫻桃詩來看氏诽,當(dāng)時(shí)的賞櫻勝地不少是私家花園事匈,如李周美中丞宅、崔諫議櫻桃園壳凳、于公花園等址敢。薛能《題于公花園》中說“含桃莊主后園深,繁實(shí)初成靜掃陰迂腔。若使明年花可待钟牛,應(yīng)須惱破事花心”,櫻桃結(jié)果了膝擂,園中很是清靜虑啤,但要想為了櫻桃花每年的盛開,園主還須付出不少苦辛架馋。
古人賞櫻桃花的熱情絕不下于今人賞櫻花狞山。張籍有一詩,講一夜新雨后叉寂,櫻桃花開放了萍启,天一亮人們等不及約人同看,急忙跑去繞樹觀賞屏鳍,以樹為圓心勘纯,在地上一圈圈留下了許多腳跡。當(dāng)時(shí)人對櫻桃花的迷戀可以想見钓瞭。
古人賞花還喜歡夜游驳遵,櫻桃花也不例外。皮日休詩“萬樹香飄水麝風(fēng)山涡,蠟熏花雪盡成紅堤结。夜深歡態(tài)狀不得,醉客圖開明月中”爱饲,秉燭夜游肢阿,花下宴飲,櫻桃花的淡淡紅色,竟像是用蠟燭熏染成的甸赏。
而在古往今來眾多賞花人中危厕,又有一人極具個(gè)性,因此留下了一段妙談硅拆。此人就是宋代宰相張齊賢之子張宗禮背渤,字茂卿奉念。此人頗事聲妓栗衍,愛混跡在脂粉堆中。有一天櫻桃樹開花鹿竭,他帶了幾位美人丽阎,飲酒花下,忽然道一句:“紅粉風(fēng)流胜溢,無逾此君谴垫!”就將妓女和侍妾都摒去了。
在別的故事里母蛛,張茂卿愛花翩剪,愛造園,時(shí)有驚人之舉彩郊,比如在高高的椿樹梢上嫁接牡丹前弯,邀人上樓玩賞。姑且不論是櫻桃花誘他成癡秫逝,還是他本來就對花木有過人喜愛恕出,只不過是被櫻桃花偶然激發(fā)出來,“紅粉風(fēng)流無逾此君”這八個(gè)字违帆,大概是櫻桃花古往今來得到過的最高評價(jià)了浙巫。
櫻桃花,美在何處刷后?
既然櫻桃沒被附加太多額外的品行的畴,一直在“以色事人”,那么在古人看來尝胆,櫻桃花的“色”究竟是什么樣丧裁?
在古人留下的為數(shù)不多的詠櫻桃花詩里,櫻桃已不止有一種顏色燎拟。以唐詩為例靶疟,劉禹錫詩中說“櫻桃千萬枝,照耀如雪天”(《和樂天宴李周美中丞宅池上賞櫻桃花》)享秒,花似雪白脂桂。白居易詩說“慢牽欲傍櫻桃泊,借問誰家花最紅”(《小舫》),又以紅為貴港驶。吳融詩云“粉紅輕淺靚妝新”(《買帶花櫻桃》)鳞乏,欣賞的又是淡粉色。不過總體來看滨靴,似還是以極為淺淡的紅色為多绝绊。方回有一首詩,說“淺淺花開料峭風(fēng)巴疾,苦無妖色畫難工收斑。十分不肯露精神,留與他時(shí)著子紅”玲躯,講櫻桃花顏色淺淡据德,是打算將紅色都剩給以后的果實(shí),不可不說是一種奇特的想象跷车。
櫻桃是先開花棘利,后展葉,這也被詩人們留意到了朽缴∩泼担“緗葉未開蕊,紅葩已發(fā)光”密强,說的就是這一點(diǎn)茅郎。這固非櫻桃所獨(dú)有,梅花誓斥、玉蘭等也都是如此只洒。但櫻花恰好與別花不同時(shí),所謂“石榴未拆梅猶小”之時(shí)劳坑,嫩葉不顯眼毕谴,花又繁密,縱使顏色不太紅艷距芬,也可連成一片霉尊,光彩奪目。
櫻桃花花瓣輕盈珍催,極易飄落紛飛督赡。李紳有一首《北樓櫻桃花》,說“開花占得春光早禾底,雪綴云裝萬萼輕磷可。凝艷拆時(shí)初照日,落英頻處乍聞鶯据鼓。舞空柔弱看無力荸刁,帶月蔥蘢似有情帅忌。多事東風(fēng)入閨闥,盡飄芳思委江城”态措,就是從櫻桃花的飄落紛飛上做文章此幕,好像飄飛的花瓣也傳遞了幾分芳思。李商隱又有一首《櫻桃花下》桑抱,說“流鶯舞蝶兩相欺签缸,不取花芳正結(jié)時(shí)。他日未開今日謝左腔,嘉辰長短是參差”唧垦,怪流鶯舞蝶破壞了花朵,又惋惜花期太短翔悠,容易錯(cuò)過业崖。

賞櫻文化,中日不同
面對“櫻”的凋零蓄愁,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反應(yīng)出現(xiàn)了顯著的不同。眾所周知狞悲,櫻花也是極易凋零的撮抓,日本人賞櫻往往偏愛它花謝時(shí)“吹雪”的景象,大抵是出于“物哀”摇锋,偏愛這種無常中展露的短暫美景丹拯。櫻桃花與櫻花不可謂不似,但是這種物哀情緒在吟詠櫻桃花的詩里幾無一見荸恕,以落花為題材的也只有寥寥數(shù)首乖酬。中國的詠櫻桃花詩里常有一種長久的快樂,白居易的一首《樟亭雙櫻樹》就講了這種快樂:
南館西軒兩樹櫻洪洪,春條長足夏陰成先俐。
素華朱實(shí)今雖盡,碧葉風(fēng)來別有情极谚。
在白居易眼中坷字,櫻桃花謝了不久就有美味的果實(shí),即便果實(shí)吃完了疲些,還有茂密綠陰可供乘涼——不知他寫這些詩句的時(shí)候通肋,是不是也想到了劉義恭在櫻桃樹下粘蟬為戲的故事呢【炜伲快樂的時(shí)光這么長璃蓬,春去花謝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究竟是櫻桃花的特性決定了我們不同于日本的賞花文化漏踊,還是文化上的不同導(dǎo)致相似的兩種花呈現(xiàn)出了不同樣貌想祝?這也許不是一個(gè)容易回答的問題吧俊伯。
?